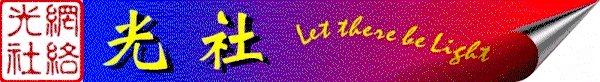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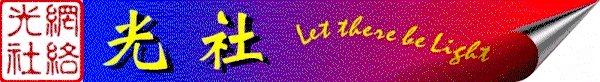
![]()
12/28/05
|
四十周年大團聚有感兼懷關存英老師 孫必達 |
| 提起筆來要在慶祝我社離校四十周年前夕寫些東西,覺得頗費思量。幾十年就這樣地過去了,人事變遷,物換星移,要報導過去的或閑話現時的都因編幅有限而不能盡言。我想倒不如藉著我們本年八月將要舉行的四十周年大團聚談談我一點感觸并順便懷舊一番。 大團聚是一件盛事,人生能慶祝大團聚的機會并不很多,更何況我們一百幾十個同學遍布世界各地要經過四十年時間後又再重聚!還記得二十五周年加冕、三十五周年溫哥華之會,每次參加的人數和面孔都不一樣,但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看看童年時代的摯友究竟現在已經變成什麼樣子?見面時聽著、講著,對發生在對方身上的事感到新奇有趣,對已經明顯有了改變的面貌覺得有點不可思議。相聚時間雖短,但大家盡情傾訴,時而爭辯,時而捉弄對方,一派童心末泯的表現,希望在這短短的時刻里可以重渡四十年前彼此同窗共學的光景。這種純真的感覺實在已達到友情發揮的最高境界。正因如此,此次大團聚帶給我們更重要的理由爭取去參加。年數越長,人心越堅,肯定以后每再隔五或十年愈覺難能可貴! 為了要把大團聚搞成功,一大班熱心的同學們早已于一年多前預它了一切安排,釆用最新的通訊科技或釆用了最原始的游說方法務必通令全社上下齊來參與盛會。最理想的當然是全体能到齊,那有多麼美妙啊!大團聚的高潮就是大聚餐,那晚簡直是「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們萬般期待這日子的到來。為什么呢?說真的、我們還是在追逐童年時代的美好時光,我們還是不知不覺地表露出我們的「童真」!另一方面,現實告訴我們全級中還是有相當一部份人不能來參加大團聚的活動的,他們或許有俗務在身,或許因個人理由,這并不表示他們在抗拒而是確有苦衷的。無論如何,我相信在考慮能否參加大團聚一事的過程中,很多同學還是內心經過一段斗爭,只有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才放棄的。所以我們在這裡可以得到一個比較現實的結論,那就無論我們怎樣刻意去安排,大團聚永遠是不能完滿的,盡管我們在爭取,總有些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人是很難或自遠都再看不到的,有時想起來心裡亦不覺戚戚焉! 寫到這裡,我忽然想起我們大家都讀過的一篇長詩,仿彿對分離和團聚有很深刻和感性的描寫,內容敘述對一個兄弟突然離世而感覺悲痛和人生苦短,對另外一個兄弟則希望能相聚多些時間但遭當時官員阻撓而感到憤慨。文章的結構是很特別并很創新,作者感情的流露不單是強烈而最吸引人的是他釆用巧妙的詞句去敘述悲痛的心情同時聯想到人生苦短,對在無常的命運前那種無可奈何的情緒表露無遺。內容中有幾句自我開解之語,我覺得可勉強適用于我面對大團聚的心情。這篇長詩就是「贈白馬王彪」,作者是漢末三國時代的陳思王曹植(曹子建),而教授我們這篇名作的正是我們尊敬的關存英老師。 在我們高中二年級的某天,風和日麗,關存英老師帶著他瘦削的身栽,微笑緩步地進我們的課室,點頭行禮后便展開書本,告訴大家今天要講授曹植的名作——贈白馬王彪!大家都記得關老師那張和靄可親的面貌,學識淵博,尤對詩,詞,曲等造詣很深,他連續教我們兩年國文,對我們中文根底的影響可說不少。聽關老師講解全文,當時只能稍稍領略到作者之意。繼而令我們背誦全方,當時覺得很順口,只是知其言而不知其所以焉!直到現在,我想起其中幾句……「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陣,丈夫志四海,萬里尤比鄰,恩愛久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后展殷勤」……這不是好像指出我們對能否參加大團聚的心結嗎?能來,當然很好,不能來,只要我們彼此永遠互相關心,就算分隔再遠亦會覺得很親近,何必時常在一起,才能對別人展殷勤?四十一年了,關老師亦已遠離我們多年,就想借此短文與同學們追懷老師的風采!四十周年大團聚將于今年八月舉行,我相信不論能參加與否都不是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心裡常有同學的影子,不時關心他們,則光社下世紀的光將會發得更亮.
|
This Page hosted by ![]() Get
your own Free Home Page
Get
your own Free Home Page